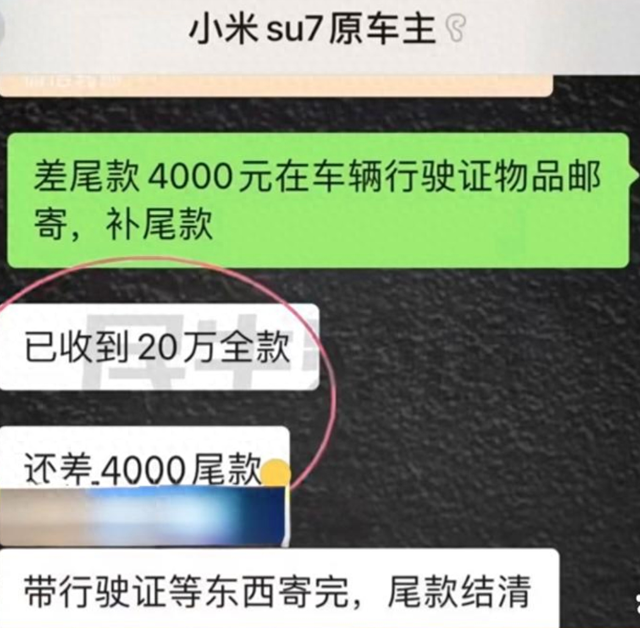1
奶奶家在上海,但是在这座超大城市郊区的某个村里。
十一假期,我回了一趟奶奶家。
老屋前后两幢,前楼三层,共有七间房,后面平房也分三间,周围大片空地开出菜园,北面临河,附近有一大片竹林,奶奶在里面养了鸡鸭。
房子三层阁楼挑出一扇窗,小时候我常爬上黑暗的阁楼,看灰尘在光线里舞动。那时老屋里四世同堂,只十几年光景,如今只留下爷爷奶奶两个人住。
少了人气,房子肉眼可见的衰败,客厅的墙皮因多年渗水脱落严重,小屋破碎的屋顶瓦片上,一株巨大的东洋草长得茂盛,丝瓜藤爬满前几年拆违留下的断壁残垣。如果不是电灯还能开,老屋前的菜地长得茂盛,很难相信这里还有人住。
回村那天,气温适宜,蓝天白云下,翠绿的稻田,风中是桂花味,狗尾巴草随风摇曳,柿子树上缀满橙红的果实。

柿子树与浇水的村民。沈猩猩/摄
这个时节的农村,美好是各种感官维度交织呈现的。
午饭后,我躺在阳光下的沙发上,在桂花味的秋风中睡着了。迷迷糊糊听奶奶说,她在村里的某片地里种了一小片红薯,让我跟她一起去翻红薯。
半睡半醒间我没有应答。醒来时,耳边是邻居小孩的奔跑嬉戏声、大人们打麻将的喧闹声、别家老宅翻新装修的电钻声、车子开出开进的喇叭声、耳背的老头老太们扯着嗓子的聊天声,村里很少这么热闹,连狗也跟着人来疯,追猫咬鸡,汪汪叫个不停。

回村的狗子。沈猩猩/摄
网上那句“回村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原来是真的,天那么蓝,空气那么清新,吵闹也成了生机。
我们牵着狗,出发去找奶奶跟她隐秘在村里的红薯地。
2
我在村里度过了童年,路就像塞尔达地图一样烙在脑中,其中很少一部分是正经的“人路”,更多是田地林间的“野路”。
要找到奶奶口中的红薯地,捷径是穿过一座烈士纪念公园,走出一片小树林,经由独木桥去到河对岸,再沿着田埂小路一直走,抵达稻田尽头的那片荒地。
烈士纪念公园又称“锡山公园”,取自本村烈士丁锡山之名,是我太奶奶的亲叔叔,他后来投奔共产党,在解放前两年遭敌军杀害,头颅被挂在村口的旗杆上。每逢过年奶奶家“做年夜”拜祖宗,总有一个火盆是烧给锡山爷爷的。
公园栽满了桂花树、垂丝海棠跟红梅,锡山爷爷的雕塑矗立在山花烂漫处,望着正前方那面党旗。
公园并不在村子核心处,背靠一片树林,平常人烟稀少。雕像下的铭文已经磨灭,难以辨析。我有时会想,锡山爷爷是否会冷清寂寞。但今天的雕像前,放着几支鲜花、两根香蕉和一面小红旗,祭拜者应该就是这两天前来的。

锡山爷爷的塑像。沈猩猩/摄
我跟妈妈也站在雕像前,合手拜了拜,继续往前走。
要走出这片林子有两条路。
一是走森林间的大路,但那有扇铁门,归护林人管,但他总是出没不定,每次经过,只能看到他散养的鸡在林间漫步,狼狗在笼里吠着,偶尔烟囱冒着烟,大多时候,铁门都是紧锁的。
于是我们选择走河面上搭的独木桥到对岸的林子里,再拐到大马路上。
这座独木桥有些年头,用破旧的条状木板拼接而成,宽近15厘米,只允许一个人通过,中间只有一根不算粗的柱子扎在河底。记得我头一次带着狗走这座独木桥时,桥体发出剧烈震动,木板嘎吱作响,狗哆嗦不敢往前走,我也害怕,连拖带拽地逃了过去。
总觉得这座桥会塌掉,但雨浸风蚀经年,每次经过,弱不禁风的它,都好好横斜在浑浊的河面上。
这次回去,它竟已经被拆除了,只剩几片破旧木板。我只能悻悻离开,绕出树林,去到大马路上走。

消失的桥。沈猩猩/摄
林间不时飞出几只鸟,我突然想起一位常住村里的朋友,他的镜头里,村子与鸟都被拍得极美。但他所在的村里近年来开出了不少精品民宿,还开了露营营地,林间有帐篷、天幕、小树屋咖啡馆……那样环境的乡村生活,是不是现代人心中陶渊明般归园田居的畅意舒心?
如果我们村也能做成这样就好了。我忽然意识到,在村里漫步时,不再只是看树、看花和看稻田,而是以收益、发展这样的目光,对乡村进行价值层面的审视。
乡村如何才算是好?怎么跟上现代发展的节奏?城里人期待中的乡村,真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们想要的吗?
我没有答案。
3
奶奶或许能给我答案。
两年以前,有人承包下村里几片稻田,改成了虾稻共生的小龙虾垂钓基地。第一年生意很好,不少人来村里钓龙虾,奶奶被雇去做厨师,日薪三百,奶奶很开心地干了俩月,还不时带回来点小龙虾。
生意最好时,基地门前那条近两百米的小路能停满车。奶奶还想过在基地门口卖自家产的鸡鸭蛋,估计也能赚不少钱。
但当我这次经过那块小龙虾垂钓基地时,已是一片肃杀萧瑟。杂草丛生,藤蔓爬满了绿色的围墙,狗尾巴草长得比人还高,完全无法踏足,只有白鹭停在河滩上,四处觅食。
基地的门依然开着,门口只停了一辆车,秋千孤零零地荡着,小卖部的招牌垂在一边。
小龙虾旺季只有初夏的两三个月,奶奶说,靠那两个月的盈利,够老板吃一年了;但也有人说,垂钓基地开业至今两年,已易主多次。虽然看不到账目,但基地招牌上残缺的字跟、参差不齐的褪色小彩旗,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龙虾基地的另一侧,是成片的稻田,稻田那头的村落就是奶奶的娘家,也就是她口中红薯地的所在。我极目远眺,依稀看到几个人影,然后根据他们走路的姿势辨别出是“谁谁的妈”、“谁谁的奶奶”,即便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再见过他们。

稻田旁的红薯地。沈猩猩/摄
她们都老了吧?不然为什么稻田里的杂草长了这么多。
我想起了爷爷,他不是在外开拖拉机干活赚钱,就是在打麻将刷抖音看网红直播——似乎就连他们也已渐渐疏远了土地。
仔细打量那片宅落,发现村里的场地上、马路上,停着与房屋数量对不上的私家车。但很多并不是回村的年轻人,而是租住在村里的外来务工者。
前两年,奶奶的寡妇姐姐送走了她们的老父亲后,年近七旬的老太把几间房子重新粉白了墙,装上了抽水马桶。距离村子十分钟车程就是东方美谷工业区,她以“间”为单位,租给5、6户在那上班的外来务工者,一个月房租就能有6千。
每次提到这个,奶奶都会嫌弃又有些羡慕地说,有了这些租金,这“刮皮姨奶奶”去菜市场“腰杆都挺起来了,买菜都更阔绰了。”
这两年,村里的民宅争先恐后地装修后出租给年轻的打工人,硬生生拉低了村里的平均年龄,村里就这样热闹了起来。
终于,在这个十月,奶奶说服了爷爷,装修工人也进场了老屋。墙皮还没铲掉,她已经想好了租金要开价多少了。
4
红薯地到底在哪里?找不到奶奶,我们只能往回走。
路过一户人家的菜园,面积有近五六十平米,一畦青菜,一畦萝卜,还有翠绿的韭菜,还没长大的白菜,田埂上种着两颗果树,无花果树散发幽香,黄澄澄的柿子压弯了枝条,河边的芦苇花洁白轻柔。
一切都长势喜人,生机勃勃。

路过菜园子。沈猩猩/摄
妈妈感叹说,如果外婆也能有这样一方菜地,一定会高兴地每天都扎在里面,不会再去小区的垃圾房边蹲着捡纸壳。
我的外婆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大半辈子都在种地。但2015年老宅拆迁后,她搬进十多公里外的大居,那里有超市、商场、社区食堂,就是没了菜园和田地。
大居里住着很多跟外婆一样的农民。他们背上锄头,在小区每个角落开荒,洒下菜籽。最初刚刚拿房时,物业管理不算严格,小区沿河那面斜坡,每到春天就会被翻得蓬松疏软,大片蔬菜鲜嫩滴翠。
外公会开电瓶车,于是他的垦荒半径更大——偶尔我们回去吃饭,外婆会盛上一碗生菜,拿出几根红薯、玉米,都是外公在小区半小时电瓶车程以外开垦的荒地上结出的果实。
在他们这一辈,人是永远无法与土地割舍开来的。
告别那片菜地走到小马路上,手表提醒我已走了4公里,耗时40分钟,而我却依然没有找到奶奶跟红薯地。

路边的田野。沈猩猩/摄
一路上我跟妈妈的话并不多,偶尔聊几句田里种着什么,妈妈回忆起,我儿时经常在田埂上疯跑,还会带着狗一起躺在稻田深处的沟渠里,回家时衣服上没一处不沾着泥。
人的记忆很奇怪,也许忘记当时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忘记了是不是被大人打骂,却记得卧在沟渠里那个傍晚,稻穗粗粝粘人的质感,跟那天的晚霞与不远处家里烟囱飘出的饭香。这种触感是如此真实,仿佛一切不过是昨天。
我也意识到,到市中心上学、工作之后,已经很久没跟妈妈这么漫无目的地散步了。我好像总是很忙,但其实也没什么事需要这么忙,只是如今的年轻人很难心安理得地停下来,总是刻意保持“毫无喘息”,否则就可能被视为不努力的“证据”。
去往红薯地的路上,我又慢下来了,在身畔千年万年的土地上,蔬菜瓜果、野草树木依然茂密生长;狗吐着舌头,疯跑在田埂上,它们在这里似乎也变得更自由。自然总是有让人平静下来的魔力。

丰收的稻田。沈猩猩/摄
我回到家,奶奶依然没有回来。但她总会踏着晚霞、拎着大袋红薯回来的。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