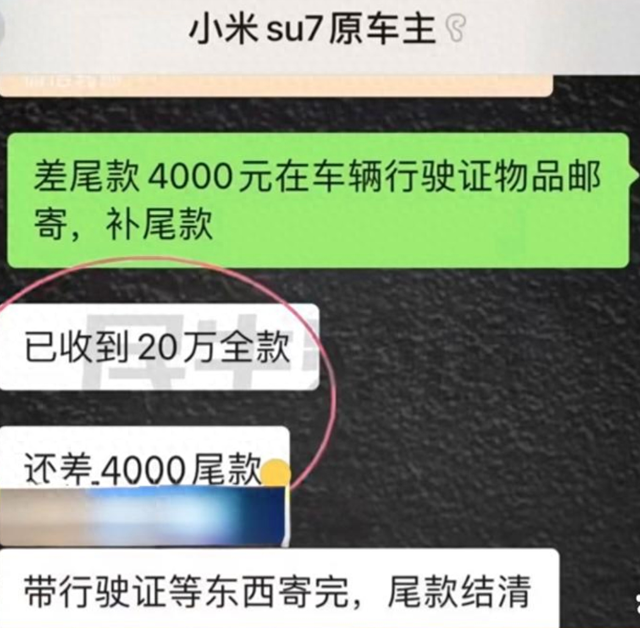新婚典礼上的充气装饰
与吕易辰正式结婚前,余斐带着上一段婚姻留下的两个孩子,来到吕易辰家中,开启了一场谈判。
余斐和吕易辰都是江西乐平人。在他们的印象中,“江西高彩礼”新闻层出不穷,乐平市的彩礼更是出了名的高。坊间流传着各类顺口溜,譬如“农村到处是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父母围着农田转,只够人家金耳环”。虽有夸张手法,却也并非空穴来风。
事实上,江西省在降低彩礼标准方面,已做过若干尝试。近期,赣州市崇义县试行了“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给彩礼金额低于3.9万元的新人家庭提供多项政策优惠,囊括了子女入学、交通出行、健康体检等方面的正向激励,试图降低当地的彩礼标准。
面对高额彩礼的风俗,余斐同样想要改变。但她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她决定与吕易辰“试婚”。
余斐直言,“我和吕易辰都三十几岁了,只想找个伴好好过日子。结婚前,我去了吕易辰家里,跟他说彩礼只要12万(元)就好。我们先过日子,互相试试看,如果合适,他再把彩礼给我。”
于是,余斐与吕易辰达成共识,展开了一场自发性的“低彩礼”实验。余斐看来,“(通过)政策(降低彩礼)总归有效果,但一时半会还是很难改变人的观念。”
在他们的故事之外,是政策难以触及的乡土人情。
高彩礼困境:“几乎每个环节都要钱”

按照江西传统婚嫁习俗,男方需要为女方购买结婚时佩戴的“三金”,包含金耳环、金项链和金戒指
胡明亮老家位于乐平市临港镇,是当地一名村干部。据他观察,就江西省乐平市而言,彩礼最高的地区便集中于盛埠村、高家镇和临港镇。这些地区的彩礼最初并不高,后来才逐步攀升。在他的记忆中,“以前也有彩礼,但1990年左右,可能才60块钱。2000年涨到几千。后来,每年涨几万,水涨船高。”
胡明亮2003年结婚,他记得,“同龄人的彩礼标准在4000元到6000元之间。我丈母娘没有问我要钱。当时,我在上海当兵,一分钱也没有。连结婚用的戒指都是丈母娘出钱打的。”他一边计算,一边向身旁的丈母娘核实,最后说道:“我丈母娘那时亏本了。”
在胡明亮看来,彩礼连年上涨是因为“女孩子少”。根据江西省统计局数据,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男性人口2339.75万人,女性人口2188.23万人,总人口性别比(女性=100)为106.92,比全国水平的104.69高2.23。江西的性别比例失调现象较为显著。
去年,胡明亮所在的社区也做了一次统计,18岁以上的未婚男性有32名,未婚女性才6名。胡明亮表示,计划生育实行时,农村的重男轻女思想显著。既然只能生一个小孩,很多人就会“想方设法”生儿子。到头来,男女双方对婚姻的需求依然不对等。
胡明亮解释,正是“男多女少”的局面,引发了婚恋市场的激烈竞争。在他的社区里,就有一名适婚少女曾从多名求婚者中做选择。“那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选择也多。第一家上门提亲的人打算给60万彩礼,隔壁说给80万。另一家说,‘你跟我儿子过吧,我拿100万’。那家的男孩子父母在深圳做生意,家境好,第二天就拿了100万元彩礼给女方,‘赢过了’其他人。”
胡明亮说,村民的攀比心,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高彩礼”风俗。“由于女孩子少,所以男方不同家庭之间就会攀比。男方给的彩礼越高,越容易讨到老婆,自然把彩礼价格‘打上去’了。”
余斐补充,不仅男方家庭会攀比彩礼,女方家庭同样如此。“有些家长觉得,你女儿拿68万彩礼,我女儿肯定得拿72万。”在“各自争脸面”的风气下,余斐所在的村里,不乏70万元至80万元的彩礼标准。
为了迎合高昂的彩礼标准,女方家庭有时候也会倒贴一部分钱。有村民提到,一户人家结婚时,女方家庭要求48万元彩礼,男方只送了38万元。后来女生说,“好了,我自己贴10万,装个脸面算了。”很多时候,为了“脸上有光”,双方家庭都蒙受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彩礼还只是花钱的开始。”余斐介绍,通常,在提亲阶段,男方及其家属会找一名媒婆,一起去女方家里,现场谈论婚嫁的条件、彩礼等。如果双方同意处对象,男方需要向女方家属送礼,每逢节假日也免不了礼金往来,单是包红包就要送出去不少钱。当然,女方七大姑八大姨也会一同去男方家里“察人家”,免不了摆几桌,给男方一些回礼红包,数额通常比男方少一些。
到了结婚当天,男方送的彩礼摆了满满一大竹筐。除此之外,还要带“四果”(包含茶叶、糖、苹果、香蕉等)、香烟,以及“三金”(包含至少4两黄金)。男方把女方接走前,还要包“奶钱”给女方的妈妈,感恩以乳汁抚养女孩长大的母亲,礼金在6万元到8万元不等。“从上轿子,到请厨师烧饭,几乎每个环节都要钱。”

江西省某婚礼上的豪华大轿。礼仪队在轿前打鼓,准备迎娶新娘
高昂的婚姻成本,引发了多层次的问题。
“孩子结婚,压力最大的是父母。”胡明亮说。村里有些男孩在田里干活,挣不到什么钱,父母就得省吃俭用拼命凑钱。到最后,父母赚的钱还没彩礼涨价涨得多,只能到处借钱,婚后还得继续还债。一位村民也表示,“我家里有两个小孩,高彩礼我接受不了。”
双田镇某村委会干部钱晓曼透露,为了降低当下的婚姻成本,当地人想过许多办法。有些男方家庭付不起高额彩礼,会要求“打欠条”。婚后闹矛盾时,女方就会提起,“你上次说那个钱,后来不还是没给我”。类似的情况发生多次后,如今大多女方家庭都不接受“彩礼欠条”,害怕对方食言,因此不答应结婚。
大约2016年左右,甚至有些单身汉铤而走险花六七万元“买老婆”,这些“老婆们”大多来自越南、缅甸。“运气好的话给你生个小孩,运气不好,老婆就跑了。警方就叫你不要买,你自己跳坑里去,那也没办法。”经过多年整治,现在“买老婆”的情况已十分罕见,村内的男子如今更倾向于和本地人结婚。但许多人依旧付不起彩礼,30岁以上的单身男性大有人在。
钱晓曼提到,高彩礼有时候还会引发财务纠纷。“有些夫妇离婚后,男方会把彩礼要回去。如果双方谈不拢,甚至会走法律程序。可是,但如果钱已经用完了,你也没办法拿女方怎么样。有时候,女方会先欠着彩礼钱,等嫁了第二家,再把前一家的钱还上。”
移风易俗之难:政策之外的乡土逻辑
尽管高彩礼引发的家庭纠纷不断,但无论是钱晓曼、胡明亮,还是余斐所在的社区,彩礼标准都居高不下。
为了降低彩礼,他们并非没有做过尝试。
胡明亮是临港镇某社区内负责“抵制高价彩礼”宣传的干部之一。“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各地要整治高额彩礼。这个规定大概也是去年才开始施行的。村干部、党员接到中央号召,就去跟老百姓打交道,推广‘低彩礼’。”
胡明亮介绍,自己主要负责口头宣传,在喇叭上录完音后,每天到外面去放。喇叭的内容大致是,“抵制高价彩礼,为了年轻人找到自己的真爱和幸福,不要拿钱作为衡量的标准。要尊重小孩意见,不要拿彩礼压制小孩,不要强制把年轻人拆散,以免伤害双方家庭。”
谈到宣传效果,胡明亮直言,“有时候,也会有领导来我们这里考察,问‘你们彩礼多少啊’,村民都回答说8万8千元。其实私底下,你要给多少钱,给多少银行卡,我们也管不了。女方肯定觉得,‘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钱总归放在自己口袋里舒服。”
钱晓曼所在的社区为了推广“低彩礼”,印刷了宣传单四处发放,但效果也有限。“开会时,布置说结婚彩礼不许超过20万元,个人餐标不超过200元,酒席不超过20桌。但实际上40桌都有。”她回忆,以前结婚时,新娘坐着两个人抬的轿子,现在却盛行八人大轿。

为了倡导“低彩礼”“零彩礼”,江西某乡镇印发了宣传单
为了改风易俗,钱晓曼只能从社交平台开始管理。她发现,很多村民喜欢“晒抖音”,在箩筐里放上一大捆钱,拍视频炫耀高额彩礼。于是,钱晓曼只要听说最近有人结婚,就会提前找到这对新人,告诉他们,“你们想拍放钱的视频可以,但不要放太多。”如果遇到放太多钱拍抖音的情况,钱晓曼会尽力找到当事人,联系对方删除视频。她说,“好事传出去没事,坏事传出去别人要学的。”
崇义县同样试行了“零彩礼”“低彩礼”家庭礼遇机制,为彩礼低于3.9万元的家庭提供政策优待。崇义县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称,此前,县里降低彩礼的方式主要为口头宣传,新规定发布后,“目前属于试行阶段,还没什么实际案例。”

崇义县民政局门口,记者未能等到前来登记的新人
针对崇义县的尝试,余斐持乐观态度。“我认为有用。你家如果有个女孩子,还有个弟弟,女孩子不要彩礼,弟弟考公务员可以加分,那肯定大家都不要了。”钱晓曼认为,“现在大家有了低彩礼的意识,彩礼可能慢慢会降下去。”
不过,钱晓曼也担心“大家可能会造假。表面上给3.9万元,私底下还是会给很多钱。”她指出,当地的婚姻和彩礼之中包含了太多人情世故。“乡下的情况说复杂也不复杂,说简单也不简单。”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指出,高彩礼背后的社会成因,主要在于江西适婚男女的性别比例失衡。女方家长想通过嫁女寻求比较高的经济“补偿”。在此背景下,彩礼越来越高,超出农村家庭年收入很多倍。
性别比例不均衡的前提下,高彩礼风俗很难改变。“如果要移风易俗,可能需要政府出面倡导。”在崇义县降低彩礼的尝试背后,固然有良好的出发点。然而,政策制定的线性思维,有时可能难以应对复杂微妙的乡土逻辑,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局变化。
甘满堂表示,“江西崇义县出台的激励政策比较难操作。例如,‘零彩礼’‘低彩礼’夫妻的子女可在学前、义务教育阶段,在全县范围内按照第一顺序择校入学。这至少是七年以后的事情。那时,相关政策会不会得到落实?另外,现在农村少子化,入学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可能激励效果也有限;男女双方家庭能否如实上报彩礼金额数量也成问题。”
甘满堂认为,农村高彩礼的移风易俗,最主要是通过乡规民约的改变。“例如村干部、党员家庭如果是嫁女儿,是否能率先响应‘低彩礼’号召?双方的长辈与子女能否坐下来协商,如男方承诺,在女方父母养老等方面承担义务?”
脱困:改变“一锤定音”的婚姻

在崇义县阳岭大道上,开了不少与婚庆有关的店铺
在余斐的观念里,很多人收彩礼的原因,就是怕吃亏。余斐认为,“彩礼”只是乡村各类礼金风俗的一部分,事实上,礼金风俗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压力。“谁都不愿意吃亏。对亲戚朋友,觉得‘我结婚之前,你们收了我那么多红包,我自己结婚一定要收一点回来’。对相亲对象,觉得‘别人能给48万彩礼,你为什么给不了’。”
然而,“不吃亏”的尺度很难把握。余斐说,“假如你结婚时,我给了你500元,过了几年,你又给我500元。我可能还是会觉得不公平。几年过去了,通货膨胀了,你还是给我500元,我不是亏了吗?你看,攀比到最后,每个人都很累。”
余斐开始思考,“如果有个人带头不要彩礼,是不是双方心里都会轻松很多?”可是,余斐毕竟来自传统家庭,对她的父母而言,“零彩礼”难以接受。
除此之外,余斐的父母还有另一层隐忧:余斐在上一段婚姻中,与前夫生下两名儿子。虽然有抚养费作为财务补贴,然而,儿子未来娶媳妇也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假如余斐拒绝彩礼,彼时,如何负担得起儿子的婚嫁费用?
余斐与吕易辰最终做出了妥协,找了个折衷方案:余斐向吕易辰收取12万元彩礼,但彩礼先放在吕易辰账上,等他们结婚满一年后,余斐再去收彩礼,两人用这笔钱共同抚养小孩。这样,双方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彩礼纠纷。
其实,余斐这样做,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她不需要高昂的彩礼,但希望儿子婚嫁时,女方也能少要一点。
“有时候,一个人就可以带动一种风气。”陆景田说。陆景田老家在石城县,是赣州市下辖县。按照他的观点,收礼习惯很多时候来自风俗压力,反过来说,如果外在的压力消失了,大家也会欢迎“零彩礼”的习俗。
“你可以搜‘江西赣州石城县请客不收礼’,上了新闻。”陆景田介绍后,又从手机里翻出新闻页面,“我们那边任何红白喜事,都不会包红包。‘请客不收礼’‘结婚低彩礼’的风俗在我们那边流行了十几年。”
陆景田回忆,“不收礼”的风俗是慢慢推进的。曾经,年年攀升的婚庆、酒席开支让所有人都很头痛,但又不得不从众随礼。其中,既有攀比心理,又有人情压力。“后来,石城县有一家人,儿子给老爸做七十大寿,扬言‘所有的人我都不收礼,我给老爸过生日不是为了收礼,而是为了让他高兴’。”
陆景田说,过了两三年,逐渐所有人都不收礼了,红白喜事从简操办。假如两个孩子结婚,双方家庭会在婚前谈话,双方敲定彩礼金额后,共同分担房屋首付、装修、买车等开支,而不是单纯让男方家庭承担压力。“一开始,村民也不习惯。可是现在,我们作为石城人,觉得低彩礼、不收礼的风俗真的很好,每个人都轻松。”
陆景田的女儿结婚时,他便告诉女婿,“你给我们家的彩礼钱,我存在银行里,我一分也不要。过个三五年,你们生了小孩或者有其他开销,就从卡里取。”
不过,根据陆景田的观察,尽管部分家庭在小范围内改风易俗,赣州市“彩礼均价”依旧不低。许多父母会自己留下彩礼钱,尤其是家里有儿有女的家庭,会存下女儿结婚收到的彩礼钱,留给家里的儿子娶老婆。另外,本地男子又倾向于娶本地媳妇,认为这样两家来往比较密切。因此,当地彩礼标准很难降下来。
谈到“高彩礼”的应对措施,钱晓曼有个建议。“我们这里彩礼多,把这个钱拿到公证处去公证一下是不是比较好?不然万一离婚,钱回不来怎么办?不公证,会有很多财产纠纷。”可是,钱晓曼同时意识到,村民对于公证彩礼的接受度较低,难免会觉得“不地道”。
钱晓曼的女儿许乐乐则给出了“高彩礼”的另一种应对方式。许乐乐今年24岁,在江西上饶市从事教师工作。她不认可村里的高彩礼风俗,干脆决定不嫁人。许乐乐所在的村子,大部分青年选择外出打工,如今分布在广州、深圳等地。外省的工作经验和观念,冲击着他们本身的乡土逻辑。一些男性不再执着于娶本地媳妇,而一些女性也不再执着于通过结婚嫁人来“回本”。
年前,钱晓曼本打算叫许乐乐回老家来相亲,隔壁村有人介绍了一名不错的男孩,说“许乐乐不是没嫁人吗?让他们加个微信,互相了解下。”结果,许乐乐扬言,“如果非要我相亲,我就出去,不回家了。”
钱晓曼拿女儿没办法,也不想干涉。“她能自己赚钱养自己。那么她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们也不需要她的彩礼钱。”
与钱晓曼在村里漫步时,墙上随处可见“农村老公,城里老婆”的标语,似乎是某种随意的涂鸦。钱晓曼解释,“这是我们村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小伙子写的,写得到处都是。他觉得本地娶老婆肯定会离婚,要去外地娶老婆。”

村民在墙上的涂鸦,写着“城里老婆,农村老公”
“近年来,娶外地老婆的本地男性越来越多。”余斐说,“彩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有些江西男人在外地打工,会和外地女生结婚。从外地带回来的老婆,彩礼比较便宜,也有不要彩礼的。”
外省传入的风俗,改变了本地看似根深蒂固的婚庆习惯。年轻人对更平等、独立的生活方式的追求,倒逼老一代的村民接受“低彩礼”“零彩礼”,甚至不婚的例外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彩礼风俗。
在余斐看来,她选择“低彩礼”,其实是降低了双方在婚姻中面对的风险,让婚姻不再是“一锤定音”的买卖。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未经允许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