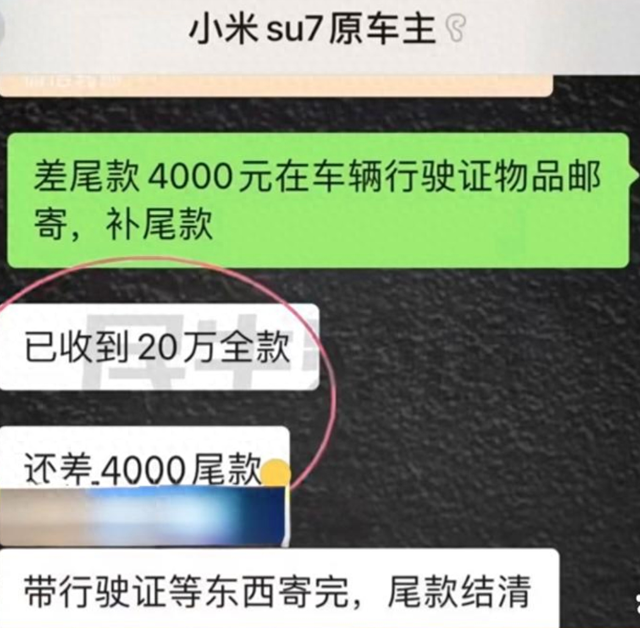中国恢复高考是哪一年(1976年恢复高考制度)。本站来告诉相关信息,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977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对中国千万知识青年而言,这场发生在冬天的考试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本文作者徐海涛就是当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考生。由于时代的原因,如果不争取高考没有机会读书,徐海涛人生最好的归宿是等父亲退休后顶替父亲,在工厂做一个工人。在那个“读书无用”作为口号盛行的年代,还有一众和徐海涛一样的青年坚信:只有读书,才有出路。那一年,有500多万人参加了高考,他们紧紧抓住了“高考”,这根命运里的救命稻草。

赶考,朦胧的命运感
每年六月,全中国都在谈论一个共同的话题——高考。我也经历过高考,虽然已过去40多年,我想起来就像是发生在昨天。
1977年10月,全国各地的广播站都在反复播放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多数知青都是从这里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的。我在农村的屋子里没有广播,但因为我家住在成都无缝钢管厂的家属宿舍,这家工厂是中央级的国有企业,由冶金工业部直接领导,所以消息来得快。家里人听到消息后,立刻喊我回家复习。
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二天一早就起来了。走了20多里的小路,赶到成都市简阳县的镇金。花了9毛钱,赶班车到简阳县城。在简阳火车站,我没有买火车票,混火车回到成都,轻车熟路地走通勤口(专门供铁路员工进出的通道)顺利出了站。
然后赶2路公共汽车。汽车不太好混,老打老实地买了票,好像是1角4分钱。经过荷花池,刃具厂,万年场到双桥子下车,我走回了钢管厂1区15栋的家。就这样,我结束了自己两年的知青生活。
1977年的高考很特殊,到12月中旬我们才走进高考考场。我的考点设在仁寿县的龙马中学,离我的生产队有30多里路。高考那天,我不到七点就起床了,步行走了3个多小时才赶到考场。一路上,天色薄薄地被晨晖擦亮,路旁田野里的冬小麦墨绿一片,染着冬霜。
上山下乡的这两年,我每个月都会到区上的粮站买国家配给的大米,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几十回。沿途的风景,小麦的长势,路面的坑洼,我都无比熟悉。但那天,一切都好像不同了。我被一种未知的、朦朦胧胧的命运感笼罩,“只要参加了高考就能去北京,就能离开农村去更远的地方。”想着远大前程就在眼前,未来有千万未竟之事等着我,我的心随着脚步怦怦直跳。
成都话说:“赚钱不赚钱,摊摊儿要扯圆。”龙马中学的摊摊儿是扯圆了的。隔老远,我就看到了“国家考场,禁止通行”的牌子,警戒线也被拉起,路都封了。
进入龙马中学必须凭准考证,我进去得比较早,先把位子找好,再出来看看环境。离开学校已经有三年了,看到学校,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却也那么亲切。两个月来,我在成都的家里备考,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一边刷牙洗脸,一边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因为政治和语文都要考时事政治。早饭后就开始早读,看书,一直学到晚上11点半才睡觉。和其他利用农活间隙抓紧时间学习的知青相比,我准备的时间很充分。对高考,我志在必得。
找到自己的位置后,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成都话叫:“先把屎尿颠干净”。从厕所出来迎面来了一个面熟的人,原来是我在成都15中学的同学刘健。还想多说两句,预备铃响了,我们约好考完再慢慢摆。
因为学习环境艰苦,那年的高考题并不难,一些题目甚至是我在参考资料上看过的。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有难度的是英语,不过英语不计入总分。
遗憾的是第一天结束后,我没有住到旅馆,只能到附近的知青家里住,三个不相识的考生挤着睡一间床,没有休息好,影响了第二天发挥。高考结束后,我按耐下焦灼的心情,心里只想着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和刘健相约着,结伴去黑龙滩旅游。
到黑龙滩的沿途风景如画,青石板路古朴,路边的旧屋雕梁画柱,飞檐斗拱。12月,天空灰黑色地沉郁着,树干斑驳,孤零零的树枝刺穿天空。景色寂寥,但呼吸着痛快的空气,我没有一丝愁苦,心情异常轻快:下乡两年多了,终于盼来了希望。尽管我是真资格的左嗓子,坐着小船随水波飘荡,我还是忍不住引吭高歌,“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之后的人生里,我走过很多旅游景点,古村古镇,把中国的各个省都跑遍了。但我还是认为40多年前的那次仁寿县黑龙滩的高考旅游是最难忘的。此后,我再也没有体会过像上次那么安逸、愉快的感觉了。
刘健还专门为这趟旅行作诗一首,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与君同舟极目观,指点此水那边山。
长青友谊行于此,万里征程始于滩。

图 | 1978年的作者(右)和刘健

没有书读,上山下乡
我对恢复高考有深厚的感念,是因为参加高考前,我在农村度过了两年的知青生活。
1956年,我出生在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从小,我就是“乖娃娃”,成绩一直都是班上最好的。1972年,我初中毕业,如果当时像现在有“中考”的话,我肯定能够考上好的高中。
但那时候没有“中考”,上高中不是看考试成绩,而是要看表现和家庭出身。光是看表现,我可以上高中,因为我在学校里面规规矩矩,喜欢学习。但是要看家庭出身,我就不行了。抗日战争时期,我爸是国民党的第十兵工厂的训导科的科长,现在被称为“抗战老兵”,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个情况还是影响了我,高中就没有上成。
只能上山下乡。当时又有一个规定,上山下乡必须要在1972年9月1号以前年满16岁,我是9月27号出生的,下乡还不够年龄。我就被安排到成都15中学去再读一年初三。
直到1973年高中扩大招生后我才上了高中。1975年,我毕业于成都17中学。那时没有高考,高中毕业生一般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被我母亲的单位成都无缝钢管厂安排下乡,归属于四川省仁寿县方家区千福人民公社大旗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
这是一个贫穷的丘陵山区,没有太高的山,也没有高大的树(据说是在大炼钢铁运动的时候把树都砍光了),山丘上长了好多灌木,农民们称之为“马桑”。水田很少,漫山遍野都是红苕(红薯)。红苕好是好,就是不经饱。不管把肚子涨得多大,一会儿就饿了。有一次我突发异想,在煮红苕前找了杆秤,把红苕连筲箕一起称,带皮一共13斤。煮熟后,我一口气就吃完了。
我下乡的时候才108斤重,回来达到128斤,脸上的肉都嘟起了。红苕就有那么厉害,像吹猪一样。

图 | 2019年,作者故地重游
农村的生活非常贫穷,我所属的生产队可能是全公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了,一个强劳动力,上工一天只有8分钱,我不算强劳力,劳动一天只能挣6分4厘钱。喷香的大米难觅,吃肉更是想都不敢想。知青下乡的那些年,肚子是不能敞开吃的,粮食要凭粮票才能买得到。大家想方设法找些东西填饱肚子,所以那时最流行的就是“跳丰收舞”,通俗讲就是找吃的。
如果要“文绉绉”一点,就是:以填肚子为目的,不择手段地把超出自己定量的,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可以吃的东西变成自己食物的过程就叫“跳丰收舞”。
既然是“不择手段”,当然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下乡的村子有蛇出没,甚至我的茅草屋里都有蛇光顾。我一锄头举起,高高砸下就把蛇挖死了。去掉蛇皮,加一块姜,洒一点盐,加一点水清炖,炖出来的汤是乳白色的,味道好极了。
农民和知青们都害怕蛇,见了蛇都叫我去打。下乡两年,我都说不清吃了多少蛇肉。现在我特别怕蛇,如果晚上梦到蛇,我都要被吓醒。

复读与焦尾琴
1977年高考后,我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甚至连高考成绩单都没有看到。但我没有气馁,重新启动了高考复习模式。
1978年,我抱着必胜的信念参加高考复习,我的父母也全力支持我参加高考。我大姐本来在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已经工作了,但是她参加了77年的高考,并且考上了成都地质学院。她的成功鼓励了我和我二姐,我二姐当时已经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作了,但还是想要上大学。

图 | 1977年作者姐姐的准考证
成都无缝钢管厂当时是国家冶金工业部直属的中国最大的无缝钢管厂,福利待遇不错,厂里专门把我们这些下乡的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开办了高考复习辅导班,不收费,只是花了五毛钱,办了一个听课证。
厂里甚至请来了成都知名中学的高中老师来辅导我们备战高考。教室则是利用子弟小学的教室,时间安排在星期天和平日的晚饭后。我们上完课以后,都不用打扫,厂里有专门的清洁队,给清洁队发加班费,请他们来打扫卫生。
不收费的高考辅导班,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现在哪有什么不收费的?但是我在高考前是确确实实享受过免费的高考辅导。
那个时候成都的各所大学也开办了各种各样的免费的高考前辅导讲座,我和几个小伙伴就骑着自行车到四川大学听过语文课的辅导。
在四川大学大礼堂里面,一位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老教授讲完了辅导课程以后,给我们讲了一个“焦尾琴”的故事,说是:吴地(今江浙一带)有个人烧梧桐木做饭,蔡邕听到火烧木材发出了清脆的爆裂声,知道这是一块好木材。他顾不得火势,立刻把手伸进灶膛抢拽出这块桐木,做成一把琴,果然,声音美妙绝伦。因为琴的尾部已经被烧焦了,所以当时人们把它叫做“焦尾琴”。
那时正是春天,窗外绿意涌动,送来一阵阵轻柔的风。大礼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大家屏息听着老教授讲故事。最后,老教授深情地说道:“你们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用自己的‘焦尾琴’弹奏出一曲美好的人生乐章,我也希望能够在四川大学与你们重逢!”坐在后排的我看不清老教授的神情,只听他的声音宽厚,我热泪盈眶,几乎要掉下眼泪。

图 | 1978年春节,作者,刘健和其他朋友
1978年夏天,我又走进了四川省仁寿县方家区的高考考场。这次,我们公社专门派了一辆拖拉机(那个时候汽车很稀少,整个公社没有一辆汽车,只有拖拉机)把我们几个考生送到区上,还给我们安排了区中学或者是公社中学的老师照顾我们的生活和学习。
此外,区上供销社旅馆关门谢客,全部的房间用来接待考生,住到了干净舒适的旅馆,一个人一间床,保证了休息和睡眠。区上供销社的食堂也成了考生的专用食堂,高考三天停止对外营业,解除了考生的后顾之忧。
这一次高考,我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考了过后好长时间都没有消息,我闲得无聊,考也考过了,就没有再扛起锄头去出工劳动了,无所事事,天天睡懒觉。
有天,我刚刚把早饭吃了,我们队上去大队小学上早读的小学生就来喊我:“徐海涛,公社通知你马上到县上去参加体检。”
我赶紧跑到公社,拿到了成绩单,总分是308分,那一年四川省的录取线是290分,我这个分数应该是能够上大学了!

图 | 作者大姐录取通知书的信封
体检过后就是填写志愿。最后,我被西南农学院录取。过后我才知道,袁隆平的母校就是西南农学院。现在西南农学院已经和西南师范学院合并了,变成了“西南大学”。不经意中,我和袁隆平成了校友。
1978年,我大姐在春节过后就进入大学学习了,我和我二姐也在秋季入学,她考上了四川财经学院,现在叫西南财经大学。大姐在66年毕业高中,二姐在65年初中毕业(她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上成高中,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大学),我是高中75年毕业的,三个人年龄相差9岁,居然在同一年进入大学学习。
这一年,是我父母最开心的一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图 | 西南大学于110周年校庆时公布的袁隆平学籍卡
– END –
撰文 | 徐海涛
编辑 | 杨柳
TAG:[db:关键词]